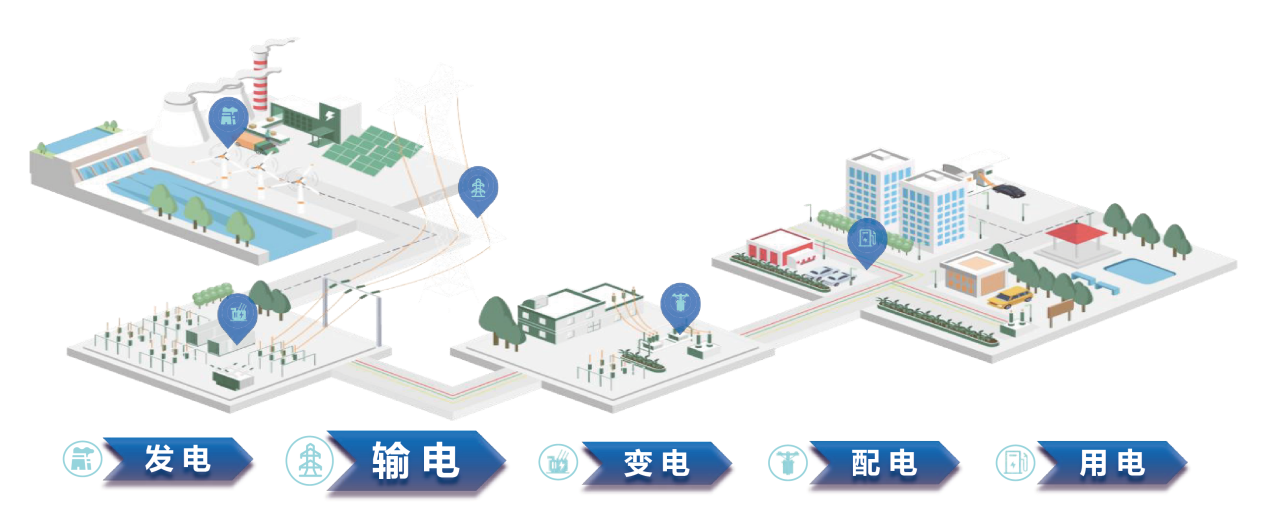《请推广学校折》的生成与价值
(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 申红珊)
【作者简介】申红珊,女,贵州遵义人,仡佬族。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学科教学(语文)专业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汉语言文学方向的研究与教学工作。为人踏实肯干,勤于钻研。

【摘 要】李端棻于1896年呈递之《请推广学校折》,在晚清王朝国家转型的危机语境下,超越了一般性的政策建言,构成一个具有知识-权力构型意涵的关键性制度文本。该奏折通过系统性制度设计(涵盖国家三级学制架构、“中西并重”的知识秩序重组、以及新型精英再生产机制),不仅为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确立了制度化核心场域的地位,更在话语实践层面形塑了国家主导型教育现代化的初始蓝图。清廷于1898年对京师大学堂的创设,标志着此文本从话语构想向制度实体的初步具象化。及至1902年以降,清廷以该折为元文本依据,推动学制系统化改革,使其内在的制度基因与治理逻辑得以在更广泛的社会空间展开实践性拓殖。这一进程,超越了单纯的机构创设,深刻介入了近代中国高等教育场域的制度化路径生成,并奠基性地形塑了其国家性、现代性与知识合法性相耦合的结构性基模,实为王朝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进程中教育治理范式重构的肇始性节点。
【关键词】李端棻;近代中国高等教育;《请推广学校折》

李端棻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所呈《请推广学校折》,实乃晚清经世致用思潮在教育制度层面的具象化实践,其以“府州县学-省学-京师大学堂”三级学制建构为纲维,破传统“重学轻教”之窠臼,倡“中西并重”之新猷,更以“选高才以充游历”之策编织人才登进网络,直指科举积弊之痼疾。尤具哲学意蕴者,在于其将京师大学堂擢升为“中体西用”之制度载体,既承太学“为国养士”之统绪,复纳西方分科授学之范式,然此“体用二橛”之设计,终使经学与哲学呈“体用互絷”之困——章程虽明定“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然实践中经学科目与西学课程终成“道器两离”之势,恰显传统“天人合一”整体性思维与近代学科分化之张力。及至戊戌后学制更迭,此折所孕之制度雏形虽为清末教育改革提供范式,然其“官僚养成所”之本质,终未脱“以技观之”的实用窠臼,距“以道观之”的哲学自觉尚存鸿渊,昭示中国教育近代化进程中"道器之辨"的未竟课题。
一、《推广学校折》的历史性生成场域
(一)甲午战败的反思
甲午战败所昭示之历史性断裂,实为传统中国治理范式遭遇本体论危机之显影。当李端棻疾呼“时事多艰,需才孔亟,请推广学校,以励人才而资御侮”(张周全:《李端棻研究资料汇编》,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16页。)之际,其奏折已深刻触及内源性治理失效与外源性冲击深度耦合所引发的教化机制系统性崩解。此际李氏之教育改革论述,实肇源于甲午惨败所触发的认识论断裂,更植根于其多重场域位置所赋予的认知框架转型,成为近代中国高等教育制度化转型之先导性制度构想。
洋务运动所标举“器物革新”,深陷“体用乖离”之形而上学困境。北洋水师之覆灭,乃清廷固守“器变道不变”认知范式之必然结果。李鸿章等虽以北洋水师为“器”之极致,然制度本体仍囿于“理一分殊”之传统治理窠臼,致海军衙门沦为官僚场域权力博弈之具,财政挹注受“纲纪之道”束缚,后勤体系陷于“名实相怨”之实践悖论。反观日本,通过《征兵令》《教育令》建构“道德的形上学”制度体系,以“无执的存有论”实现兵员征募与人才培养之“体用一源”。此役本质乃两种文明本体论范式之交锋:清廷以“中体西用”割裂道器,而日本则以“性体开显”之实践理性重构制度本体。福州船政学堂等新式学府虽引入西技,然课程体系仍依附“礼制”官僚架构,未能完成“格物致知”之现代学科建制。生徒既被摒于科举“正途”之伦理共同体,复遭士大夫“以道观之”之价值排斥,陷入“所学非所用”之存在论异化。此即严复所洞见:“中国所本无者,西学也,则西学为当务之急”(严复:《严复集》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0-41页。),然若仅“徒袭西学之形貌”而拒斥制度本体革新,终将堕入“形神离决”之现代性困境。
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学制令》(1872)所构建之教育体系,以“邑无不学之户,家无不学之人”(叶立群:《日本的教育改革》,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第23页。)为纲,确立三级学制及强迫入学制度,实为“理气一元”哲学观之制度实践。其以朱子学“格物穷理”为基底,融摄西方实证精神,形成“教育—科技—军事”良性循环之“体用一源”范式。至甲午战前,日本小学入学率达40%,东京大学等高等学府建成,彰显制度形上学之实践效能。反观中国,1895年全国新式学堂不足40所,教育体系呈现“道器相离”之结构性断裂。李端棻考察日本后痛陈“日本变法以来,广兴学校,译书授业,故能强本弱末,雄视东方”(梁启超:《变法通议》,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8页。),其《推广学校折》中“自京师以及各省府州县皆设学堂”(张周全:《李端棻研究资料汇编》,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17页。)之三级架构,实为对《学制令》“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制度哲学之自觉效仿。
李端棻教育革新之历史意义,在于突破“中体西用”之认识论桎梏,尝试建构“道器相嬗”之制度形上学。其奏折所提藏书楼、译书局、仪器院、报馆、游学五端,实为以“格致诚正”重构知识生产体系之制度设计。此构想虽未脱“礼制”框架,然已触及严复所言“本无”之制度本体——即通过教育制度之形上学重构,实现“心性论”支撑下器物层与制度层之辩证统一。甲午战后教育改革之深层逻辑,正是以日本“性理开显”之实践理性为镜鉴,解构“理一分殊”之传统治理范式,推动中国教育由“器技移植”向“道体重构”之范式转换。
(二)李端棻与《请推广学校折》
李端棻作为同治二年(1863)进士,其思想根柢深植于儒家“通经致用”之脉系,尤以山西学政期间整顿书院为典型实践,彰显“经术”与“治术”的体用相即(张昭军:《从“经世致用”到“中体西用”——张之洞对传统儒学的调适和锢蔽》,《孔子研究》2004年第4期。)。其虽为清流核心,然暗合《周易》“革”“蒙”二卦精微:恪守“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圣外王之道,复倡“师夷长技”的变革路径,形成“旧学为体,新学为用”的调适性思维结构。此种张力具现于广东乡试重时务策论、拔擢梁启超等举措,实为科举制度“旧瓶新酒”式的隐性突破。至《请推广学校折》主张创构京师大学堂,更以“蒙以养正”(《周易·蒙卦》)为易学依归,将儒家“内圣”工夫转化为“开民智、育新民”的外王实践。晚年归黔办学,终以“致良知”精神践行乡邦教化,完成“治统”向“学统”的本体论回归,为儒学现代转型提供“道器合一”的诠释范式。
李端棻思想演进深植晚清“体用之辩”的哲学场域,早期囿于洋务派“中体西用”范式。光绪十三年(1887),其教育革新思想尚拘泥“算学、天文、舆地、格致”等形器之学。甲午战后认知发生本体论跃升:洞悉日本明治维新成效源于“国民认知图式转向”与“国家理性化治理架构”的精密耦合,遂超越洋务派“头痛医头”模式,在《推广学校折》中直指“非天之不生才也,教之之道未尽也”(张周全:《李端棻研究资料汇编》,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17页。),将教育鼎革提升至制度重建高度。此认知转折呼应维新派“尽弃旧习,再立堂构”的体用观革命,其奏折所陈四事——“御门誓群臣、开懋勤殿议制度、改定六部则例、派朝士归办学校”(赵青:《中国近代教育奠基人:李端棻》,贵阳:贵州出版集团,贵州教育出版社2022年版,第211页。)——彰显对政教制度“本体”的重构意志,标志晚清士大夫对“中体西用”范式的自我扬弃。
《请推广学校折》之酝酿植根甲午后经世思潮勃兴,康南海《上清帝第四书》首倡“设议院以通下情,开学校以育人才”,以“三级设学”架构奠定形上学基础(康有为:《康有为全集·第一册》,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78页。);严几道《原强》斥传统教化“偏德疏智”之弊,立“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三纲重构国民性;梁任公《变法通议》更申明“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罗炳良主编,梁启超著:《变法通议》,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18页。),凸显教育为体用转换枢机。李端棻通过强学会论辩及与严复、黄遵宪等符号互动,完成异质教育理念的本体论整合:学制取法康氏形而上学架构,课程承袭严复“体用不二”认识论,将格致实证精神注入“普通学/专门学”二元结构;制度设计则融摄黄遵宪《日本国志·礼俗志》的“冲击-反应”史观。三者共构规范性秩序——学制立文化认知合法性,课程载价值理性,科举改制与经费保障成规制性控制,形成历史必然性的教育制度形构。
较之同光改良方略,李端棻擘画以“中体西用”为枢轴构建三级学制:小学课“识字、习字、读经史子及舆地算术之浅近者”,中学增“天文格致农务工艺商务之学”,大学究“专精一业”(张周全:《李端棻研究资料汇编》,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17页。),形成“蒙养—经世—穷理”的格致阶序。其创设册府(藏书楼)、器局(仪器院)、译曹(译书局)以补西学资源,更以“变科举”弥合“学优则仕”古道与近代知识生产的裂隙。此设计既超越康南海“废八股兴学校”的泛道德诉求,亦突破张之洞《劝学篇》“中体西用”的体用二元困境。其“仕学院承道统存政教之本,师范馆立师道育新民,译书局通中西转知识”的三足架构,既暗合西学“经验领域分化”哲思,复以制度理性实现“道器相济”。戊戌年孙家鼐依此制《京师大学堂章程》,完成“教育行政机关”向“最高学府”的价值理性制度化转捩,更启导癸卯学制使晚清教育自“器物移植”升华为“制度本土化”,终成传统经学解构与现代学科建制之底层逻辑。
二、制度蓝图的诞生:《请推广学校折》的体系化构建
(一)先“破”后“立”的奏折逻辑
《请推广学校折》所揭橥者,乃晚清科举制度所衍生的本体论困境与主体性异化之深层危机。八股取士以僵化形式理性桎梏士人思维,致其沉溺章句训诂而疏离经世实学,酿成“才智不伸”之存在性压抑。此制度性异化使儒学道德实践性沦为工具化操演,士人主体性于科名崇拜中遭客体化,形成“饰正藏邪”之价值理性塌陷。当西学东渐引动文明范式冲突,传统教育之认识论封闭性更显其与格致新知断裂,终致国势衰微的文化系统性危机。尤可辨者,科举制度对“理一分殊”之割裂,使天理流行滞于文字窠臼,士心困于“理气二分”之认知迷障。
针对此困局,李端棻以“体用一源”为纲构建新式教育体系。其以官书局、大学堂为经,藏书楼、仪器院为纬,形成知识再生产网络——藏书楼承文献考据之统绪,仪器院启实证格致之门径,二者暗合“道器相即”之认识论重构。译书局与报馆构成西学本土化之诠释学通道,经由概念转译实现中西义理互释;游历制度则为知行转化枢纽,使士子在时空经验拓展中体认“天下大同”,终以经世致用达成主体性复归。此多维架构通过制度与心性互动,使中等资质者得“格致诚正”之自励,奇才异能者臻“成己成物”之境,恰如程伊川“显微无间”之理势相成。“十年以后,贤俊盈廷,不可胜用矣”(赵青:《中国近代教育奠基人:李端棻》,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集团,贵州教育出版社2022年版,第185页。),此预言实为理势相因之必然,彰显“翕辟成变”的文明更新机制。
(二)高等教育制度的核心设计(新式教育体系的系统建构)
李端棻于《请推广学校折》中构建的“州县学(小学)—省学(中学)—京师大学(大学)”三级学制,实为晚清“中体西用”思想在制度层面的具象化实践。府州县学以“选民间俊秀子弟年十二至二十者入学”,承袭传统蒙养教育之“格致诚正”精神,旨在奠定“修身明伦”之德性根基;省学则“选诸生年二十五以下者入学”,(张周全:《李端棻研究资料汇编》,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17页。)以经史为体、西学为用,呼应张之洞“新旧兼学”之训导,培养“通经致用”之中层人才;京师大学堂“选举贡生监年三十以下者入学”,其定位超越单纯学府范畴,肩负“为天下表率”之双重使命:一方面以“十科立学”重构知识生产范式,打破经学“一统性知识垄断”,将传统“四部之学”解构为分科治学之现代体系;另一方面赓续国子监“明体达用”传统,要求师生“砥砺德行,匡正时俗”,以儒家伦理维系“士林精神气质”。此三级学制通过“层级贯通”的设计,实现“理一分殊”的教育哲学理念,使个体修齐治平之进阶与家国治理需求形成结构性契合。
“十科立学”方案以经学为文化根基、史学为治国借鉴、格致学(含算学、物理等)为科技载体,更纳入政治、农工商等实务学科,标志中国知识分类从“通儒之学”向“分科治学”的范式革命。其深层逻辑在于“中西会通”原则下对“体用关系”的辩证重构:经史之学“固其根柢”维系文化主体性,属“体”之存续;西学实务“拓其才识”呼应现代性诉求,属“用”之拓展。此种分科体系突破洋务运动“器物层面”效仿之局限,通过政治科培养新政官僚、兵学科服务军事改革、农工商科支撑实业救国,使学术与国家治理形成“知行耦合”。尤值瞩目者,京师大学堂通过译书局系统译介《天演论》等西学典籍,并以“仪器院-实验室”开展实证研究,促成“旧学新诠”与“西学本土化”之双向知识流动,终结了“有技术移植而无知识创造”的洋务困局。其学科设置更直接介入新政实践,如宪政编查馆成员三成出自大学堂教习,彰显“经世致用”从思想倡导向制度实践的转化,实为传统儒学历经“体用之辩”后形成的制度性回应。
(三)主体性制度创新
主体性制度创新彰显体用赅备之辩证思维。李端棻奏议所倡“中西教习分科聘任”机制(张周全,《李端棻研究资料汇编》,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18页),实乃“明体达用”思想在师道范畴之具象化实践。其通过“令中外大吏各举才教习之士”的擢拔路径,分设经史政教与格致实学两途:前者延揽本土通儒执掌心性义理之学,后者聘西士专授农工商医诸科。此种划分殊非全然技术性安排,实暗合“理一分殊”之认识论框架,既维系“道统”主体性,又涵化“器识”之开放维度,使生徒在“理气互发”的教化场域中达成“格物致知”与“诚意正心”的辩证统一。至若藏书楼、仪器院之创设,则昭示“知行相资”的实践论转向。藏书楼广纳寰宇典籍,非惟文献庋藏,实为“道问学”提供文本凭依;仪器院陈设泰西机巧,亦非器物罗列,乃使“即物穷理”获得实证根基。此种硬件建制突破“重道轻器”传统窠臼,将“尊德性”与“道问学”统摄于“经世致用”的文明重构进程,为心性修养与实证精神提供具象化载体。
国际接轨方略折射文化主体性之自觉调适。游学制度与译书局之并举,深蕴“理势相因”的历史辩证法。前者倡导“周游列邦以观其会通”,非止技艺习得,更在“观其玄枢”——透过现象洞察西方文明之“本然之理”,此乃“即用以求体”的认识深化;后者系统迻译泰西典籍,实为“格义”方法论之现代转进,既需“训诂考辨”确保义理之准确传达,更须“以中化西”完成术语的本土转化,如将“philosophia”译作“哲学”而非“理学”(林美茂,赵淼:《为什么是“哲学”?——关于西周的选择与追求探因》,《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2年第1期,第61-72页。),彰显文化主体性的诠释自觉。二者形成“体用贯通”的双向循环:游学者携“西学真源”归国反哺译事,译著凭“中学根基”重塑知识范式,恰如“阴阳燮理”般促成“理一分殊”的文化整合。此种制度设计超越“中体西用”之机械二分,在“道器相即”层面达成“返本开新”的创造性转化,使晚清教育改革成为中华文明“旧邦新命”的实践注脚。
三、从文本到机构:《请推广学校折》与京师大学堂的制度化
(一)首倡京师大学堂
李端棻《请推广学校折》之奏议,实为晚清教育制度变革之枢机,其文经《时务报》刊布而寰宇震动,足证其教育本体论重构之时代价值(此现象本身,恰印证李端棻创构京师大学堂诸策之历史必然性)。虽经戊戌政变之劫,惟京师大学堂得存,昭示中国近代化进程之韧性。光绪二十二年(1896),孙家鼐《复议开办京师大学堂折》承李氏三级学制之思而深化,倡言“添筹经费、分科立学”乃教育实践之要义,更以“中国京师建学乃通商以来创举”揭示制度移植与本土化之张力。(余世存:《北大读本》,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3页。)其筹办六事——“宗旨宜定、学堂宜造、学问宜科、教习宜求、生徒宜选、出身宜广”,实为“中体西用”思想之制度具象,标志着教育价值取向由传统科举向近代分科知识体系之范式转换(赵青:《中国近代教育奠基人:李端棻》,贵阳:贵州出版集团,贵州教育出版社2022年版,第195页。)。
然守旧势力以“经学惯性”阻滞变革,致京师大学堂延宕至光绪二十四年方得施行。梁启超痛陈:“李端棻之奏深切详明,得旨允行而恭亲王刚毅等谓可缓行,诸臣和之,虽奉明诏而束高阁三年矣。”(梁启超:《梁启超自述》,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1页。)及光绪颁《明定国是诏》厉行变法,明示“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遂成“经世致用”思想之制度突破。梁启超所拟《奏拟京师大学堂章程》乃中国首部近代学制纲要,其以“中西总教习分治”(许景澄掌中学、丁韪良掌西学)体现知识论之二元整合,使大学堂兼具最高学府与国家教育行政机关双重本体论位格,统摄全国新式教育,开国立高等教育之先河。(赵青:《中国近代教育奠基人:李端棻》,贵阳:贵州出版集团,贵州教育出版社2022年版,第196页。)此制不仅为北大、北师大之滥觞,更奠基中国农大、西北师大等学统,彰显教育层级结构之现代重构。
后世学人皆以李端棻为近代教育哲学之奠基者。陶行知于教育本体论层面指认:“晚清学务倡行者如李端棻、孙家鼐等,其制度建构皆以人才教育为价值核心,乃救时济世之实用理性体现。”(陶行知:《中国建设新学制的历史》,璩鑫圭,唐良炎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053页。)周谷城更从政治哲学维度强调,李端棻的教育改革在全国具有原创性作用。他说:“李端棻,旧任仓场总督,于光绪二十二年(公元一八九六年)(原文为光绪二十一年,属错误表述,特此更正。笔者注)奏设京师大学堂及各省学堂,实开教育救国论之先声。”(周谷城:《周谷城全集》之第一卷《中国政治史》,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05页。)对此,贵州大学的钟家鼎先生持同样立场。钟家鼎先生说:“李端棻的《请推广学校折》开启了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崭新篇章,奠定了中国近代教育制度的基础。直至后来《壬寅学制》和《癸卯学制》的面世,其中都贯穿了《请推广学校折》的巨大影响力。”(钟家鼎:《李端棻与<请推广学校折>》,《教育文化论坛》2011年第4期,第64页。)李氏之历史位格,正在于以制度性突破实现传统教育“体用不二”之现代转捩。
(二)京师大学堂章程对奏折的继承和制度延续
李端棻《请推广学校折》所建构之教育制度框架,在《京师大学堂章程》中实现了体用层面的赓续与制度化转进。该章程作为近代学制体系之圭臬,深刻承袭李氏奏折“三级学制”之形上架构,以“小学—中学—大学”的纵向衔接体现“理一分殊”的教育本体论。其“溥通学与专门学”的分科范式,既是对李氏“十科立学”说的实践性扬弃,亦暗合“道器之辨”的哲学分野——溥通学涵摄“经史义理”之体,专门学统纳“西艺西政”之用。尤值申论者,章程特设“藏书楼”、“仪器院”专章,将李氏“器以载道”的物质文明观落实为制度存在;而《学生出洋游学》章节及译书局之设,更使“中西兼赅”的认知论通过制度安排具象化。然制度实践必受历史理性制约,章程实际仅立道、政、农、工、商五科,相较于奏折宏图实存“格致未彰”之憾,此乃师资阙如、资源困绌等经验世界限制所致,彰显制度理想在经验场域中“经权之道”的辩证调适。
戊戌变局虽使维新受挫,然李端棻制度设计的内在生命力经由张百熙《钦定学堂章程》(壬寅学制)获致历史性升华。壬寅学制以“蒙学—小学—中学—高等学堂—大学堂”七级链条,将三级学制细化为“理气相即”的有机系统。大学堂分科扩至经、法、文、医、格致、农、工七门,既补苴章程之阙遗,更以“分科立学”实现知识论的现代重构。张百熙明定京师大学堂为“通国之纲领”,实将李氏“自京师至府州县皆设学堂”的经世理想,升华为“体用一源”的中央集权式教育治理范式。其课程体系虽仍标举“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的纲常本体,然分科教学及日语优先原则,凸显“西学为用”从器物层面向制度层的渗透。至癸卯学制更系统确立“中体西用”宗旨,使李端棻“中西并重”思想终成制度定谳。壬寅学制所创“通儒院”(研究生层次)作为学制顶点,既圆融“格物致知”的传统认知链条,亦开“道问学”现代转型之先声,使李氏教育哲学通过三段七级之制完成“理—气—物”的范畴具现化(周浩《壬寅学制——中国学制近代化的起始》,宁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第20-22页)。癸卯学制虽为近代首部全国实施学制,然其框架实植根于壬寅之制,而壬寅之精神血脉则可溯至李端棻奏折所蕴之经世致用哲学,终使中国传统教育在体用张力中实现“旧邦新命”的制度蝉蜕。
四、奠基性关联的延展:从京师大学堂到国家教育体系的奠基作用
京师大学堂(1898年创立)的诞生与发展,绝非仅仅建立了一所高等学府,它实质上是中国现代高等教育与国家教育体系的制度孵化器。其复校(1902年)后的实践,深刻塑造了北京大学的内在基因,并为中国近代教育体系的构建奠定了不可动摇的基石。
(一)对北京大学制度基因的塑造
京师大学堂作为北京大学的前身,为其注入了独特的制度基因,使其自诞生起就承载着国家最高学府的使命与现代化内核。
首先,1904年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癸卯学制)明确规定:“通儒院(相当于研究生院)设在京师大学堂内(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北京:中华书局2020年版,第100页。)”,大学堂毕业生“予以进士出身”,大学堂总监督“秩视侍郎”。这从国家制度层面确立了京师大学堂作为全国教育体系顶端的、拥有最高学术地位和荣誉授予权的“最高学府”地位。这一法定身份被北京大学完整继承,成为其核心身份标识和追求卓越的内在驱动力,奠定了其在现代中国学术版图中无可替代的至尊地位。
其次,京师大学堂初创时已有分科雏形(如仕学馆、师范馆)。其制度基因的核心突破在于1910年正式开办经科、法政科、文科、格致科(理科)、农科、工科、商科共七科。这标志着中国高等教育首次系统性地采用现代大学的分科(院系)制度,彻底打破了传统“四部之学”的框架。各科设置章程详细规定了学制、课程、师资要求,为北京大学乃至中国现代大学的学科结构、专业设置和人才培养模式确立了基本范式,直接推动了学术研究的专门化和深化。
最后,京师大学堂初创即设藏书楼,重视典籍收藏。这一传统在北大得到发扬光大,其制度基因体现在对系统性知识积累与开放获取的追求。1918年落成的北京大学图书馆(红楼),由李大钊任主任,采用杜威分类法,开放阅览,迅速成为当时亚洲规模最大、管理最先进的现代大学图书馆。这不仅是硬件设施的飞跃,更是将现代图书馆作为大学“学术心脏”的理念制度化,为北大的教学科研提供了坚实的知识保障,树立了标杆。
(二)对中国近代高等教育体系的奠基作用
京师大学堂的实践,尤其是其复校后与壬寅、癸卯学制的紧密互动,使其成为中国近代高等教育体系当之无愧的“制度母体”。如癸卯学制(1904)作为中国近代第一个颁布并全国施行的学制系统,其核心架构——三段七级(蒙养院、初小、高小、中学堂、高等学堂/大学预科、分科大学、通儒院)——并非凭空产生。它是对京师大学堂复校实践中已先行探索和确立的层级结构(预科——正科/分科大学)的全盘继承与系统化扩展。并且京师大学堂自身就是癸卯学制中“分科大学”和“通儒院”层次的唯一实体模板和最高标准。它的存在与运作,为全国各级新式学堂提供了清晰的升学目标和效仿对象,是学制得以“标准化”并推行的关键枢纽。
此外,癸卯学制规定各省城应设一所高等学堂(大学预科层次)或分科大学。京师大学堂的学科设置、课程体系、管理模式成为各省创建新式高等学堂的直接蓝本。如山西大学堂(1902)的中西斋分设(后整合),北洋大学堂(1895创立,1903重建)的工科、法科设置,均明显参照了京师大学堂的分科理念和课程内容(如重视西学、外语、实用学科)。京师大学堂的毕业生和教员也常被聘至各地学堂担任要职,直接传播其制度经验。这种自上而下的制度复制与辐射,迅速构建起一个以京师大学堂为顶点的全国性高等教育网络雏形。(邓红利:硕士论文《“癸卯学制”述论》,华中师范大学,2007年,第26页)
京师大学堂的非凡意义,在于它同时完成了两项历史使命:它作为“北京大学”的前身,塑造了这所中国顶尖学府追求卓越、引领学术的制度基因——从法定的最高学府地位、现代分科体系到世界级的学术设施传统。更重要的是,通过癸卯学制将其探索的分级架构、学科设置、管理模式等核心制度要素标准化、法典化,并辐射至各省大学堂,最终奠定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体系的基本框架和运行逻辑。从一所学堂到一套国家体系,京师大学堂的实践深刻证明:制度的创新与落地,是教育现代化转型最核心的驱动力。
李端棻的《请推广学校折》,其历史意义远非一份普通的政策建议。它以其前瞻性、系统性与可操作性,为中国教育制度的近代转型绘制了一份纲领性路线图。《请推广学校折》的价值,不仅在于其思想的先进性,更在于它成功地将京师大学堂塑造为实现其制度理想的“孵化器”与“发动机”。通过京师大学堂的创办、复校及其在学制制定中的核心作用,李端棻构想的国家三级学制、中央教育统筹、现代教学内容等关键要素,从抽象的文字转化为具体的、可操作的、全国性的制度安排。壬寅、癸卯学制的血脉中,流淌的正是《请推广学校折》的思想精髓,而流淌的载体,正是京师大学堂的实践探索。可以说,没有李端棻的蓝图,近代学制的构建将失去方向;而没有京师大学堂作为其制度落地的核心支点,这一蓝图也难以如此深刻地塑造中国高等教育的百年基业。李端棻与京师大学堂,共同完成了近代中国高等教育制度奠基的“第一推动”。其遗产,深刻烙印在中国追求教育现代化的基因之中。